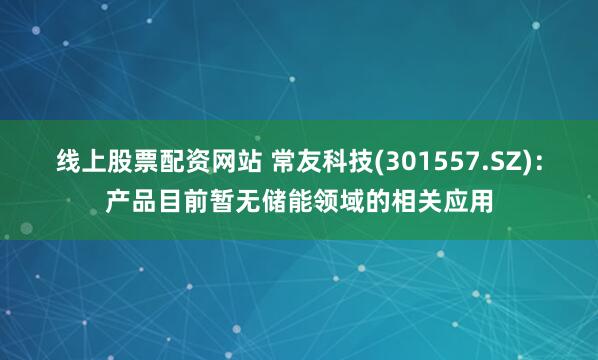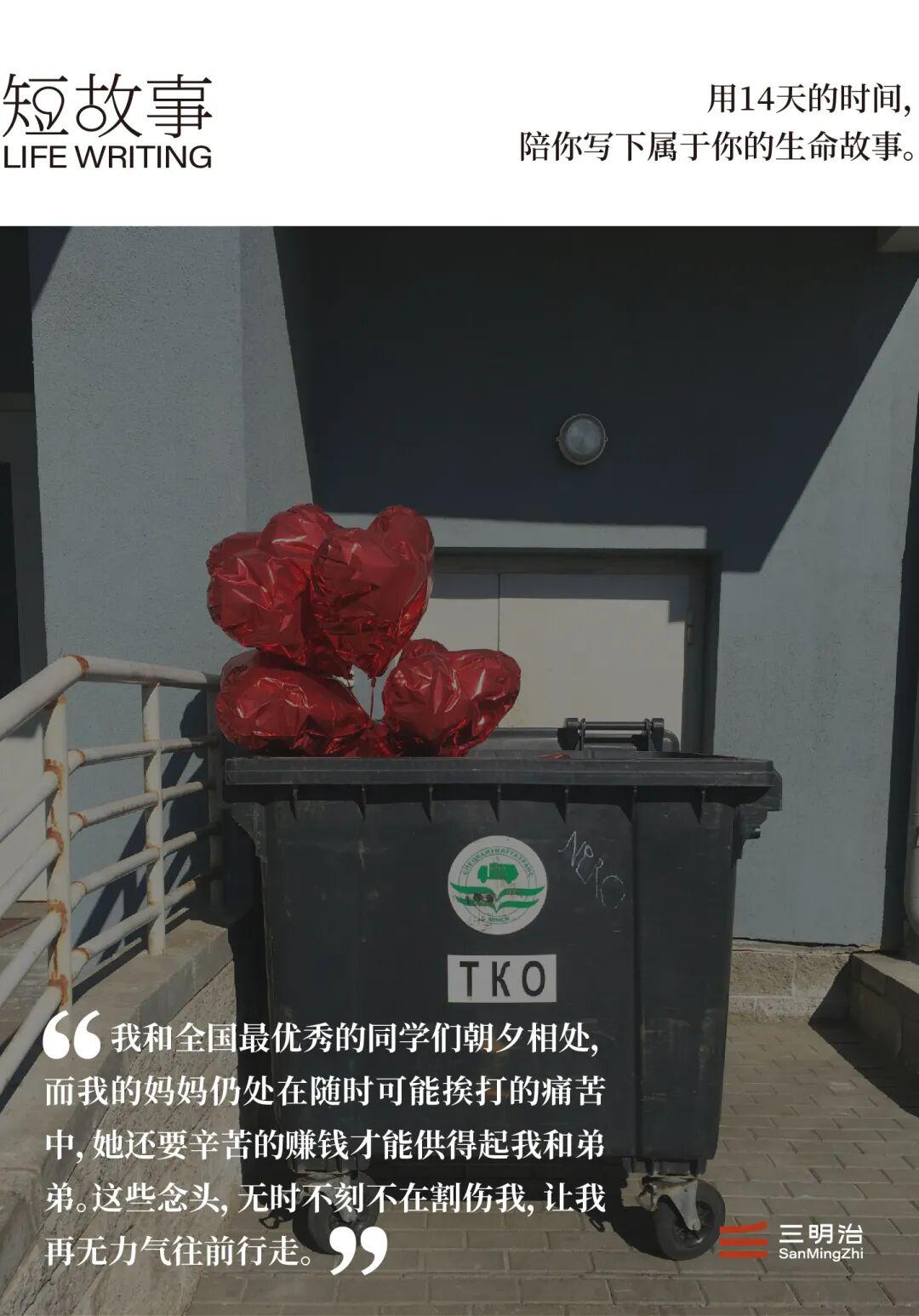
文 | 如一线上股票配资网站
编辑 | 渡水崖
1
妈妈,我曾记得幼时被你惊艳过的一幕。
那时奶奶家住在自建房,房子在二楼,要从一楼的大门进来,穿过堆满杂物的一楼才能上来。那天你骑着刚买不久的摩托车,停在楼下的门口,我趴在二楼的窗边看着你,兴奋地喊妈妈。
那天你刚刚去烫了直发,长发及腰,爽快地散在空中。你面容圆润,气血充盈。你抬头望向我,用中气十足、却像黄鹂一样明亮的声线冲我说:“妈妈来啦,快下来!”
当时的我年纪还太小,好像还没有开始学语文,所以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。但那一幕像照片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。
现在的我,愿意用这样的词汇描述那一天的你:飒爽、英气、温柔又有力量。
而二十年后的你,疲态、下沉、充满怨恨地看着我,向我砸过来一些毫不留情的话语。“你就这么不知道感恩?”“我们家不是什么有钱人,能给你花这么多钱去读书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。你怎么学得这么自私冷漠?书都让你读成邪教了吗?”
你已经骂了我,半小时?四十分钟?我也不太清楚了。只是当年那副惊艳过我的画面突然掠过脑海,和后来的你相比显得颇为割裂。我甚至想笑,但我只敢在心里笑一下,毕竟我怕你觉得我又在高傲地嘲笑你。
打从我考上985开始,你就觉得我对你“趾高气昂”了。只是我没能在毕业后及时找到好工作,这件事情似乎给了你一个反讽我的理由。
“毕业了遇上疫情,知道工作有多难找了吧?”我一边听着这些话语,胃里在翻江倒海,可我却只敢沉默,我甚至不敢有一个表情。“上学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早点找实习?让你别去读研了,索性找个工作算了,你不听,非要去。”可是妈妈,当时不顾一切也要让我去读研的也是你呀。人的记忆是可以这样随意被话语修改的吗?我不明白。
你常常说自己半辈子都风险给了我,似乎你一切的不幸,都是我造成的。可你一边怨恨着,一边又全力支持着我的学业。每当我失败,你就悔恨投资失败;每当我取得一些进展,你就欢欣鼓舞。好像我一边吸食着你,一边又成就着你。
2
我常常在想,如果你当初选择了离婚,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?
记得那是他第一次打你的夜晚。他喝醉了酒,一边用浓重的西北方言恶狠狠地骂着你这个“臭婆姨”,一边痛快地用尽方法打你。其实我记不太清细节了,那个时候我太小了,好像只有三岁,也可能我不想记得。我只记得第二天,家里来了很多人,有爷爷奶奶,姥姥姥爷,甚至还有舅舅、大姨和二姨。客厅的墙上有新鲜的血迹,鲜红地爬在雪白的墙上,非常显眼。你用凄厉的声音控诉着他,你的丈夫,我的爸爸。可没能换来任何一个人同样的控诉声。那时我什么也不明白,我只知道好像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最后的最后,好像是爷爷沉重地叹了一口气,就离开了。
后来我爸告诉我,那一天好像是你们第一次谈及离婚,但没能谈成。具体是因为什么,是缺乏娘家人的支持?还是爷爷也象征性地教训了他几句?我已经无从得知。后来你们告诉我,那一天我爸曾将我抱在怀里,问我,爸爸妈妈如果离婚的话,你跟谁呀?当时我没有回答,只是“哇——”得一声吓哭了。他说,你们因此才没有离婚,都是为了给我一个健全的家庭。
是呀,一切都是为了我,一如既往。
后来的每一场酒后家暴中,大多时候,你都将战场拉到你的卧室,试图将我的房间留作一片净土。偶尔暴力的程度超乎你想象,再也收不住的时候,你会来我的卧室,匆匆忙忙地喊我“赶紧穿衣服收拾书包”,然后带着我逃走。在很多个黑夜里,你拉着我逃出家门,跑出单元门口,吹到楼下的晚风,我就知道我们得救了,这天晚上的战斗终于结束了。
每当这些夜晚,你都会带着我窘迫地到别人家借宿。这些“别人家”,我印象中有爷爷奶奶家、叔叔婶婶家或是大姑家。你几乎没带着我回过姥姥姥爷家。是因为傲气吗?还是在你的世界里,娘家早已经是靠不住、你也不想再去靠的去处了呢。
我一直是一个性格有些奇怪的人,经常对别人缺乏信任。任何一个人伤过我一次以后,或轻或重,我都很难再与对方相处。朋友说我这样就叫做“傲气”。我在想,这或许也是从你这里遗传来的吧。
后来你还提过很多次离婚,往往是因为和我爸又发生了冲突。你提的时候带着太多的情绪,让人甚至分不清你是真的想离婚,还是只想抒发心中的愤怒。而每一次你控诉完后,又会带着些自我宽慰原谅他:“看看他这次会不会改进吧!”
尝试又放弃的次数太多,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被搓磨了锐气,再也提不起逃脱的力气。
3
对于我的教育,你从来都很费力,甚至过分费力。小升初时,我考上了全市前列的私立中学,你好像发现了我的另一种潜力。在此之前,你坚持让我学舞蹈和乐器,风雨无阻。用你的话说,这叫“培养艺术细胞”。但我知道,你是在我身上实现自己未竟的理想。
你是家里的老小,从小睡在家里的阳台上,直到中考结束,你考上了中专。你学的是幼教专业,会安排你们学习钢琴、舞蹈、画画等艺术类入门课。你的同学们有一些已经自己买了专业的绘画工具,或是买了自己的乐器。可你没有,你一直怨恨,姥姥姥爷没能给你一点点支持。
打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摆着一架电子琴。你会握着我的手教我弹小熊跳舞,那是你学生时代唯一练熟了的曲目。从三岁开始,你开始带我学舞蹈,六岁起学古筝,并孜孜不倦地监督我练习,发现我有任何懈怠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呵斥。
我好累,也好怕,妈妈。它们不像是我的兴趣,更像是任务。而当我终于抓住“学业”这根救命稻草,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包袱甩下肩头,理由是“我要专注学习”。但我后来才发现,也许我并不是对这些事情发自心底地厌恶,只是我再也扛不住你厚重的期许了。我可以弹琴,可以跳舞,只是不想再被你拉到亲戚朋友面前像猴戏一样表演。
后来的日子变得像雨天的雾气一样氤氲、模糊。我努力地学习着,在同学面前假装着开朗,其实生活中偶尔穿插着被凶狠的呵斥、被砸碎的家具还有一声声“妈妈都是为了你”的余音绕梁的咒语。
4
如果一切只是这样单纯地走下去,或许一切还有转机,可世界上最令人无奈的就是“永远没有如果”。
对于我的性别,你好似始终都有些遗憾。你曾对我说,其实你第一胎就想要男孩的。但我在出生前给你托梦,说,“妈妈,我是女孩子,请你不要失望。”于是,你也就此接受了我这个女孩。
直到你36岁那一年,毅然决然决定再生一个男孩。
我很想问你为什么当初做了这样的决定,可我知道现在的你对此也只剩下满心的后悔,因为弟弟并不想你想象的那样和我一样优秀,甚至体格弱小,经常生病。我猜,你当时是觉得家里条件还不错,我爸的兄弟们都在努力的生儿子,你不能丢面子。甚至,你试图用生儿子来挽救那内里已经破碎不堪的婚姻?你们是不是还觉得我是一个可靠的长姐?我不敢往下继续想了。直到我踏入社会之前,我都从未觉得自己和“长姐”这样味道陈腐的词汇沾过边。
可笑的是,有了弟弟也没能让他有一丝一毫的醒悟。他依旧放纵着自己,一副毫无负担的浪子模样。于是夜间出逃时,你需要带着的“拖油瓶”又多了一个。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夜晚,你又一次带着我逃出生天,但弟弟刚刚一岁出头,你无法在挥舞的拳头下再抱着他离开。于是我听到他打电话来威胁你:“臭婆姨,赶紧回来,不然我闷死你儿子。听见了没?”
我忘记我们有没有因此回去了,只知道弟弟幸运地活了下来,又或许他也舍不得真的闷死自己的亲儿子吧。
“爸爸”这个词,在我的幼年和青春期时期都代表着一个“时而会变身的野兽”。当他没有喝醉时,往往是烦躁的,对一切都很没有耐心,但嘴上不说什么。喝醉后的样子,嗯,相比不必我再多说。没能和他离婚的你在任何一个他没变身的时候用尽全力羞辱他,你明媚的亮色声音变得尖锐而刺耳,不知休止地批斗着、嫌恶着他。而当他化身为黑夜里的怪兽以后,又要软下你黄鹂一样的嗓子,低声下气地求他停止施暴。你们像一对太极八卦图一样,此起彼伏着,但就是分离不开。
其实你们的开始,还颇为有趣。当年你从幼师毕业,没机会进幼儿园,世界在一无所有的你面前展开。你那个时候在客运单位工作,可以跟着车队走南闯北,还能拿点工资去西安、兰州买漂亮的衣服和耳环。也是在这个时候,你认识了我爸。他长得帅气又会玩,又有城市户口,在车队里已经是最上乘的选择。于是你们很快地谈恋爱、结婚。你大概也想不到,结婚后的他竟然会是这般模样,而你们的性格也这般不合适吧。
而他有一个让你舍弃不下的优点,就是把家里的钱全部都给你管。后来你还去百货商店做过售货员,可生下我后不久也放弃了,毕竟他那些年的收入确实还算不错。当然了,你的说辞又是“为了我的学习”。我不相信他没有私房钱——他也的确被你识破过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年轻时他赚到的大部分钱都收归你的掌控之下。我也因此获得了穿漂亮衣服,上价格高昂的雅思补习班等等的机会。
或许在同学们眼里我还算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学霸,可只有我自己知道,其实我内在也是一个怪物。一个难以以真面目示人的怪物。一个怪物和另一个能制衡怪物的女人生出来的小孩,能是什么正常人呢,你说是吧?
5
时间总是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。后来弟弟也长大了,在学校经常受人欺负。为了避免他被霸凌,你开始为他寻找合适的私立学校。而这个时候我爸也终于意识到,原来养一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,是会绑得他没办法继续荒唐无度的。你们为这个老来得子操碎了心,衰老快速地爬上了你们的脸庞。
记得那是2010年左右,客运车辆在一年内频发安全事故,我爸赖以生存的行业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规定的限制。而高铁也在那些年像藤蔓一样快速地生长、密布,他的合伙人们开始对生意的前景心生疑虑,最终因分配争议而互相猜忌,就此分道扬镳。好笑的是,年轻时你和他都认为“钱嘛,多好赚”,总是挥霍无度,导致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。而到了中年,生意溃败、儿子弱小、家庭情感稀薄,现实的打击倒是让我爸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生龙活虎,竟然钻进了厨房这个小天地,每日三餐,做得不亦乐乎。这让你感到迷惑:难道他年纪大了,知道悔改了?
然而,这点虚浮的安慰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毕竟现实里的一个个问题还是冷酷地横在面前,让你避无可避。很快,你们也很难再支付得起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,弟弟不得不重新回到公立学校。而我即将面临高考,是家里唯一的“翻身希望”。你看看在厨房里含着支烟闷头做饭的丈夫,只能重新拾起服装生意,开店赚钱维持家用。
可你毕竟错过了那个猪都飞得起来的年代,这个时候的实体经济远不如你年轻时那么繁荣。你心态从来都不好,时而进账颇丰、时而不开张的日子却像是过山车一样刺激。你开始埋怨自己命苦:年轻时容忍家暴的丈夫,吞咽委屈生下儿子,怎么还是换不来一点点好运?还有这个女儿,她凭什么成绩这么好,架得你在孟母的高座上下都下不来?凭什么为了她能好好学习,她妈要每天辛苦奔波、好吃好喝供着她?她知不知道她妈为了她受了多少委屈,她凭什么就这样心安理得地享受?——“等她考完了,我可一定要让她知道知道,她妈我有多不容易。”
6
妈妈,或许你不清楚,或许你知道了却选择视而不见,其实高三的那一年,我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
我知道你们都指望着我,指望着我能够“光宗耀祖”,毕竟家里近两代人都没有一个大学生。我看到以往花天酒地的爸爸在我回家后再也不会开电视,好像在高三一年也没有酗酒撒泼过一次。我看到曾经像怨妇一样的你每天对我笑脸相迎,不论是早中晚,桌上永远都摆着营养均衡的饭菜。本就内敛的弟弟也被你们严令呵斥“不准打扰姐姐”,于是他不敢靠近我房门一步。我从未享受过这样国王一般的待遇,可这宁静却诡异的日子却并没让我放松下来。西北的天,几乎每天都是晴朗的,可这样的青天白日怎么总是照得我浑身冒冷汗呢?它仿佛要把我藏了很久的阴暗角落全部都扒出来,一丝一缕,细细密密地晾出来,看看它们有几斤几两。
高三一个平静的午后,我在家结束午休,拿起桌上你给我准备好的保健品。家里很安静,为了不打扰到我,你带着弟弟出去散步了。但我其实没睡着——打从高三开始,我就染上了失眠的毛病。那天不知怎么的,平时都很听话的药瓶,却怎么拧都拧不开。我扭头望了一眼墙头挂着的表,每一根针都在平稳地挪向上学的时间点。我忽地把药瓶举起,砸向墙角。它终于开了,胶囊撒了一地。我捡起两粒吃了,把剩下的那些用扫把扫进簸箕,拢一拢倒回了药瓶。
那天晚上,你笑盈盈地问我是不是把瓶子掉在地上了,“妈妈看到门口撒了两粒药”。我点了点头,我们继续吃你做的清蒸鲫鱼、清炒茼蒿和蒸鸡蛋。
终于熬过了我的高三那一年,你也终于不必再“忍气吞声”了,你开始像开闸泄洪一样控制不住地向我抱怨、诉苦。毕竟我可是享受了你一年“弓腰伺候”的人,怎么能不抓紧让我记得你的功劳,将来好对你感恩戴德呢?
是命运的推手吗?我超乎预期地考上了颇有名气的985,按照我平时的模考成绩是远远够不上的。这破天的“富贵”砸得你不知今昔是何年,好像这一年来的忍辱负重、忍气吞声都有了报偿。哦不,一切都是你的功劳,“没有我,她肯定连个大学都考不上!”你喜滋滋地陶醉在自己的伟大里,这样自顾自地想着。
7
去北京以后,我开始自然而然变成了你手中的提线木偶——你一边幻想我走上了一条闪闪发光的“带领家族翻身”之路,一边又迫切地害怕我飞得太远。于是你一遍又一遍地用几百个字的微信消息提醒着我:“你妈妈我还在这个泥潭里,你可不要忘了哦”。虽然我远在北京,我的四肢,我的头顶,我的心脏,都始终挂着一根线,线的那头是身在那座西北小城的你。
可现实是,一直不断向飞向更宽广的世界的我,早已经和你之间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我面对的一切是你从未见到过的。哦不,其实你见到过。当我的同学们在自信大胆地参加社团、谈恋爱,和教授辩论学术观点时,我却困于自卑不敢上前,尽力地隐匿自己——熟悉吗?其实和你在职高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只是你自卑的理由是缺钱,而我的自卑,源于虽然我和全国最优秀的同学们朝夕相处,而我的妈妈仍处在随时可能挨打的痛苦中,她还要辛苦的赚钱才能供得起我和弟弟——这些念头,无时不刻不在割伤我,让我再无力气往前行走。
于是我度过了兵荒马乱的大学时光——我成绩一般般,没有找到自己下一步的方向,更没有谈恋爱。我也不知自己怎么了,明明高中可以卯足力气学习的我,在大学却总是静不下心。四年时间转瞬即逝,我的成绩不足以保研,更不敢肖想出国读研,虽然这是大部分我的专业的同学们在做的事。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选项,申请香港的学校。香港没有英美那么贵,但至少听起来也像是去留了个学。我们有谈论过,去香港读书的费用是不是会加重家里的压力,可你的孟母精神总是在这种“关键时刻”条件反射式地被激发:“你不论如何都要去,已经没让你去英国了,香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供你去。”
在香港的那一年,他除了偶尔还是会酗酒和大吵大闹,但已经没什么力气对你和弟弟拳打脚踢了。而不酗酒的时候,他就勤勤恳恳地工作。你们将他每个月的工资打给我做生活费。你好像开始有些原谅他了,甚至似乎忘记了他曾经的残暴。当一个人期待干枯的泥潭开花太久,是不是哪怕它长出几根杂草,都会欢欣雀跃?
8
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。按照你的期待,你们都已经这样辛苦地“把我的学历供出来了”,总该享受享受女儿出去工作,反哺父母的舒服日子了吧。
可是,人生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变好,但却不会按照你的计划突然变好。我毕业那年,刚巧碰了新冠疫情爆发,我的简历更被瞬间结了冰似的招聘市场甩到角落。说来也好笑,法律行业里,开放给应届生的好的岗位竞争极其激烈,而在疫情之下,更像是群狼争食;不好的位置可就多了去了,但只有小几千的月薪。而我呢,既挤不进去前者,又不想屈就后者——家里已经经济压力这么大了,我怎么好再做一份连自己都养不起自己的工作呢?
于是,毕业后长达一年的时间,我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这个事实让你难以接受——毕竟你对我的期待是毕业就能手拿高薪,变成在CBD叱咤风云的都市丽人。我不仅自己光鲜亮丽,我还可以解救你们于水火之中,弟弟的后半生也有了姐姐作为靠山,他就再也不用努力了。
雪上加霜的是,你的店面也因为封控而被迫直接关停。那段封闭的时光里,你该付的货款一分不少,可进账却是纹丝不动的零元。而事实是,疫情之前,你其中一家店就在开业仅仅几个月之后关门大吉。选址失误也罢,经济不景气也罢,原因都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你们在我的学费基础上,又背上了一笔欠款。
2020年,在封控的最初几个月里,你的眼里尚且还能容得下我。而后来逐渐解封后,日子一天天流逝,你看着我一次次面试和落选,开始认为是我辜负了你一直以来的辛苦付出——一切都怪我没有在大学就力争上游,不从大二大三就开始努力找实习,不在大四就布局好工作选择,这样连留学的费用你们都不用出。
是啊,你之所以过着凄惨的生活,都是因为我。为了给我一个健全的家庭,你忍着家暴的痛苦也不肯离婚;为了让我好好上学,你放弃了分明在那个年代可以赚到钱的工作;为了让我能不要放弃到手的香港offer,你宁愿自己受苦,也要给我付学费;甚至——这个弟弟都是为了我生的,因为她像让我老了以后有个陪伴。
而你呢,我猜,你当然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,你永远是最无辜、最凄惨的受害人。弟弟是一个可怜孩子,他不仅身体不够健壮,还要从小就处在姐姐的光环带来的阴影之下,夹着尾巴做人,怎么能开朗得起来呢?而丈夫也年纪大了,已经很少酗酒了,这些年也很少再动手,甚至还知道给家人做饭,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只有这个女儿是罪魁祸首,而家人一个个都在为了她而受煎熬,她享受了一切,却一点不知道感恩,真是天杀的,你怎么能养出这样一条白眼狼?
9
当你把这一套荒谬的逻辑摆到我面前的时候,我是懵的。
我知道打从大学以来,你就对我产生了不满。哦不,其实你的半辈子都在围着我转,四分之一在围着我和弟弟转。我只是不知道,怎么刚刚毕业,我就成了你一切不幸的源泉,你的丧门灾星。
愤怒吗?当然。委屈吗?尤甚。可是我实在不知该如何跟你争吵。或者说,我从来都不会。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背着一个包袱——要让妈妈开心,妈妈不开心,就是我的错。更何况,你的这套故事编得实在精美,严丝合缝。好似我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挑起一根线来,你都能把它拽回去,重新拉得齐齐整整。
我赶紧找了份并不符合预期的工作,就逃也似的离开了家,不敢再多待一天。离开家以后,你开始要求我“还债”,每个月给你打钱。可你没看到的是,我这些年曾面临病态的职场霸凌,屡次在工位上偷偷流泪,却始终不敢停下来。直到爷爷留下的老房子终于等到了拆迁,你们也不再扛着包袱时,我天真地幻想自己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审视一下接下来的路,可还是面临你的反对——你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,一种将我的“回报”当成理所应当的义务的习惯。
我曾和你激烈地对峙,试图用反叛让你“醒悟”,可最终没有一次不以失望告终。后来我们多次爆发争吵,关于那一条条你对我耳熟能详的指控:白眼狼、不知感恩、卸磨杀驴、冷血……直到后来,“翅膀”终于真的硬起来的我,竟然失去了力气抵抗这些攻击,留下的只有满心的心疼。
10
你曾也是那么明媚的一个女孩啊,但你亲手把她杀死在那个决定不离婚的夜晚。
但我深知这不是你的错,她死于你、爸爸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,和这个社会的共谋。他们太过强大了,强大到你不敢出一丝声音来反抗。于是你将那个天真的自己杀死,和他们同流合污。
可她只是死了,不是消失了。她的尸体就那样俏生生地横立在你心里,扰得你片刻不得安宁。所以你一边不离婚,一边控诉着我爸的一切恶行和不作为;一边羡慕我甚至托举着我,使我自由地追求海阔天空,一边又扭曲地控制着我,怕我飞得太远,反证了你曾经因为懦弱而杀死那个她有多么错误。
当我终于足够独立时,我再也不敢反抗你。或许你明白我压根没做错任何事,或许你也知道自己的控诉是多么地离谱,或许你刻意的合理化自己的一切举措。这都不重要了,我只能尽力地让自己飞得更远,让你的托举有所价值;也尽力地呵护你的言辞,因为我不忍心让你面对已经错了二十多年的惨痛现实。
妈妈,如果可以的话,我多么希望你像那年下午一样,活得自由,飒爽,富于生命力又充满了温柔。妈妈,我宁愿不要后来这一切你加诸在我身上的光环,我宁愿舍弃后来得到的任何一件让你面上有光的名号,也想和你过着平凡且清甜的日子。只是妈妈,我知道这一切都回不去了,你已经活在了为自己写好的故事里,再也出不来。
一天,我和ai聊起关于你对我造成的钝痛,它温和地告诉我:“当一个落水的人在水里拼命呼救,你要做的不是立马跳下去救她,而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,找到你所需要的工具和援助力量再去施救。否则,你只会被她拉下水,一起牺牲”。
妈妈,我想我救不了你了,我也只是一个小孩。那个明媚的你恐怕早已被你判了死刑,沉入海底。而我能做的只有放开你的手,才有机会代她看到真正的光亮。
妈妈,再见;妈妈,我们一定会更好。
写作感想:
写完之后,其实没有想象中的“痛快”,只是我更加明晰了,关于妈妈,关于父亲,关于我。我意识到经历都将成为我创作的土壤,而这片土壤,正是我曾经一寸一寸低下头,用真诚为自己耕犁出来的。
谢谢自己,也谢谢渡渡老师,她在每一节中都能很温和却精准地指出我没有敢正视的问题——一次都没有逃过。于是为了将这篇我珍视的作品填充完整,我不得不一次次重新梳理心中的恐惧,这是不可多得的体验,因为人在自循环中,总是会忽略很多问题。
这趟旅程,不仅是写作技法的提升,更是一个厘清自己的过程。算是今年八月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吧,带着这份清晰,我才能更好地和自己相处,走向更适合自己的方向。
今天的文章来自「非虚构短故事」工作坊,
报名9月短故事(9.16-9.30):



大师工作坊
虚构写作
非虚构写作
剧本创作
诗歌
里所诗歌工作坊
每日书
7月共写班(每月开展)
7月自由书写班(每月开展)
English Daily Writing(每季度开展)
点击查看更多

在地写作
写作生活节
点击查看更多


大师工作坊
虚构写作
非虚构写作
剧本创作
诗歌
里所诗歌工作坊
每日书
7月共写班(每月开展)
7月自由书写班(每月开展)
English Daily Writing(每季度开展x
新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